网上有关“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明朝的西藏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形式来确立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的.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大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为安抚应招前来归附朝贡的藏区各僧俗首领,逐授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封号.如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获得河州卫指挥同知官职;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获得炽盛佛宝国师封号;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获灌顶国师封号;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卜获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封号;僧人答力麻八刺获灌顶国师封号.同时,明太祖还
先后对前来归附和请官的大批西藏故元官员授予了新的官职,这些官职大抵有:乌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挥司同知、指挥佥事、宣慰司使、巡检司巡检、招讨司官、万
户、正副十户、百户等等.不过,明洪武年间,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封显然还带有较大随意性.这着重表现于两点.其一,当时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
封,有相当数量是应西藏僧俗首领的要求而进行的.如大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大规模授官职,均是应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要求和荐举.答力麻
卜刺与公哥坚藏卜的受封,亦是两人主动“请师号”的结果②.其二,从明洪武年间明朝所授官职和封号的名称来看,不仅多而杂,而且较为混乱,其中有不少只是
沿用元朝的封号和官职罢了.这之中因人设官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少.故《明史·西域传》载:“初,太祖的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
明太祖所以对西藏僧俗首领这样大量授官封号,大致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意在安抚.明初,西藏各僧俗势力无疑是将明朝作为元的继承者看待,因此,他们竭力向明朝请官请封,不仅是沿袭元朝以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做法,而
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在西藏取得稳固与合法地位以及争取自身实力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政治需要,这正是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明初频频向明请求封号官职的原因.而
明太祖在这方面大力满足他们的需要,采取“来者辄受官”政策,这在政治上对西藏各僧俗势力乃是极人的安抚.
其二,明朝在政治上同样需要通过对西藏僧俗首领的授官封号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朝贡关系来体现其对西藏的统治主权.明朝对接受封号与官职的西藏各僧俗首领明确要求他们承担其政治责任,即“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③
大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
“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
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借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
以官职,如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明期洪武朝,明朝封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
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刺.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
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
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明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者仅为“大国师”和
“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
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明朝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三十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斯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大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诰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准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大明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大明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工”,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大明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
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大明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
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十九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
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大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大明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
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问、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
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朝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
起了一般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子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大明永
乐年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大明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调整的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整分封重点和对象.即将洪武朝时期以授职官为主的分封改为着重授予教派领袖以封号的分封.也就是说,在分封对象上把西藏宗教教派领袖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洪武时期在分封上突出职官系统而忽视僧人作用的弊端.明成祖在分封重点和对象上的这一调整,显然意在利用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和保
持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相吻合.
第二、提高分封规格和等级.针对洪武朝时期对藏族僧人分封规格偏低情况,明成祖大幅度提高了对僧人的
分封规格,在所封僧人名号中,以“法王”为最高等级、“教王”次之,以下依次为“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等,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新
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等级制度.值得强调的是,明成祖首次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实行的普遍封王做法,不仅是对洪武时期西藏政策的重要变革,而且也?重大发展.
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第三、充分注意了分封的地区性和代表性.明成祖时期受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其各自的教派如下:
大宝法王:噶玛派;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阐化王:帕竹派;赞善王:灵藏派;护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派;辅教王:达仓派.
其中,噶玛派、帕竹派和止贡派是噶举派的分派,达仓派、灵藏派是萨迦派的分派.由此可见,在明成祖分
封的三大法王和三大教王中,基本上无一遣漏地囊括了西藏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
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从分封的地区性来看,大宝法王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大乘法王在后藏,即最西,大慈法王在
前藏,居二者之中,这样的分封布局,体现了明成祖精湛的政策构思.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势力范围各自占有东部、
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为准,其设置了三大法王,于其间的小空间配置了五名教王,当是依据当时西藏的现实、了解了全部情况后
的决策.当我们知道这些教王的封爵几乎都在永乐时代授予时,对于明成祖关于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当,更加感叹不止了.”④永乐时代这种充分依据西藏各教
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使明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
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西藏分封政策的调整,无疑使这一政策更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分封作为对西藏体现和行使其主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仅止
于分封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主要针对受封者
制定,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例贡”.即各受封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进行的朝贡.例贡的宗旨是让西藏受封的各僧俗首领以
定期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形式来表示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这种朝贡实际上成为西藏受封的各实力派首领对明朝中央承担的一项特殊政治义务.例贡通常三
年一次,但在大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
2.袭职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王和
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至此完成袭职手续.重要首领,
特别是诸王的承袭一般均由朝廷遣专使往封.这种袭职朝贡,成为明朝制约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重要手段.
3.谢恩、贺庆朝贡.当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之后.也要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如弘治八年,大乘法王陆竹坚参巴藏卜,灌顶国师藏卜领占各遣人朝贡,“谢恩袭职”.此外,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如宣德元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国师班丹扎思巴、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扎夫“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
很明显,明朝对西藏各教派首领的分封并未徒具形式,原因就在于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的一套严密的例贡
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其以分封来体现的对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与西
藏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途径.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如何来保证朝贡制度的顺利实施?即明朝以什么措施来确保西藏大大小小的各受封首领能按照规定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
我们知道,明朝与西藏的情况和元朝和比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明朝在对西藏的施政上至少存在两个不利
因素.首先,明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缺乏象元朝那样的紧密宗教联系.虽然在表面上,明朝统治者(尤其以明成祖为代表)同样优待西藏宗教首领,但这并
非象元朝统治者那样是出自宗教上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皈依,而更主要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正如佐藤长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完全不认为宗教在个人生活
上有需要,他所以优待哈立麻,决非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无疑是由一种政策的立场而出发的”⑤.实际上这不仅是明成祖,也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统治者对西藏宗教
的基本态度.由于明朝统治者并不真正崇信和皈依藏传佛教,这不但导致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也使他们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
不可能有象元朝那样的特殊宗教联系.从而决定了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已经不可能以其同西藏教派势力的宗教联系为基础.其次,明朝既不象元朝那样是通过对西藏地
方政权的直接扶持和支撑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同时明朝对西藏权威地位的确立和维系也不是象元朝那样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明朝虽然也在西北驻军布防,但主要目的是为对付北方的蒙古并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北方蒙古始终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劲敌,双方之间战争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以任何武力方式或强制性手段来作为对西藏施政的基础也已属不可能.所以,明朝唯一的选择是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这一点,在明朝推行朝贡制度方面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反映.
对于明王朝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因此,朝贡
制度对于明王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而明朝在推行朝贡制度方面无疑采取了一种极明智而又实际的作法,这就是对前来朝贡者回
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来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
这一作法始于明初,当时,明太祖为了安抚前来归降入贡的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除授其官职外,还给予厚
赏.到明成祖时,由于对西藏采取积极经略态度并大肆分封和优宠西藏宗教首领,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也日益丰厚.如大明永乐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入朝,成祖先后赏
赐七次,其中仅金、银两项每次约以百、千两计,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丝绸彩缎、钞锭等.明朝的赏赐一般分为正赏和贡品价赏两种.正赏是根据朝贡者身份和
地位高低而给予的赏赐,正赏数额明朝前期无明确规定,大明成化以后,对一般喇嘛僧人进贡者的正赏数额作了如下规定:“喇嘛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
表里,纻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阔生绢四匹,纻丝衣一套,内二件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
十斤.从洮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纻丝并绫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
但诸王的正赏远不受此数额限制,尤其是请王亲自入贡者,赏赐往往非常隆厚.贡品价赏则是给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大多根据贡物品质高低、数额大小相应给赐.
如对进贡马匹均一律给价,宣德前所进马匹不论等第高下都同一给价、大明宣德元年始规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纻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纻丝一
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纻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⑦.明朝赏赐的对象包括遣主、使者和随行人员三部分.使者和随行人员的赏赐
在朝贡时颁给,遣主的赏赐则由使者带回.对于地区较高的遣主,如诸王等,朝廷还往往派专使赍物回赐之.除实物赏赐外,来京使者一般还有赏宴,留边听赏人员
的食宿也由当地官府供给.此外,西藏朝贡使团在内地的往返,均由明朝政府沿途驿传提供食宿,“水路递运船,陆路脚力”,并配有伴送人员为其办理登记,过关
手续等.
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⑧,如果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
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这种优予贡利的作法,对西藏各大小地方首领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大明
永乐年起,西藏僧人即渐渐突破明朝规定的三年一贡的入贡期限、开始频繁入贡.如大明永乐七年,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即两次遣使朝贡,大宝法王从永乐
七年至十年,每年皆遣使入贡.由于所有前往朝贡人员均能得到赏赐,而明朝前期对朝贡人数并无明确限制,故导致了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的逐年剧增.大明宣
德、正统年间,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至二、三百人,到天顺年间则猛增至二、三千人.可以想象,当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浩浩荡荡地穿梭于西
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终绎不绝,赏赐不赀”.这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所以,从大明成化以后,明朝在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
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相反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
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项规定.第一,乌恩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凭验入,以杜混冒.⑨
上述限制措施显然并未完全得到执行.为此在大明隆庆六年明朝不得不再次作出如下限制性规定:第一,将国师、禅师、都指挥使等的袭职朝贡一律并入年例贡
内,袭职后不许再差人谢恩进贡.第二,规定未及三年不许来贡,“不愿者不强”,凡贡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贡者,参作下次例贡之数.第三,鉴于使团规模日渐扩大
的局面,不得不在限制赴京人数基础上相对放宽诸王贡使数额,规定阐教、阐化、辅教三王,大乘大宝二王“俱三年一贡,每贡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赏,在京题
给,五百人减赏,本省给与.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赴京,余留边听赏.护教王三年一贡,每贡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赏,三百八十八人减赏,全赏内起送六
人赴京,余留边听赏”⑩.
不过,除了在大明万历以后明朝对西藏朝贡次数和人数的限制真正有所成效外,在从永乐朝到隆庆朝的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无论在次数和人数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大明成化八年,礼部奏当年岷、兆等卫奏送各族番人共四千二百余人,除给马值不计外,凡赏彩缎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锭.这里还主要是从西北来的藏族,并不完全是乌思藏的朝贡者.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阐化工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同年,大宝法王、牛耳寨(阐化王下属官)派来谢恩、请求袭替或新招抚的头人使人共一千四百七十人.
大明弘治十二年,乌思藏及长沙西宣慰使司各遣人来贡,贡使达二千八百余人.
大明正德五年,大乘法王遣使达八百人.
大明嘉靖四年,乌思藏、长河西、长宁安抚司贡使过额者达九百四十三人.
大明嘉靖十二年,乌恩藏及朵甘贡使达千余人.
大明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
明朝治藏历史的治藏政策
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 文化 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形成,一起来看看。
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形成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茶叶产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都不产叶。四川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种茶、 饮茶 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中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 其它 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天顺二年(1458)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鸟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
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__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茶马古道历史文化价值
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恻的 故事 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回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形成相关 文章 :
1. 关于茶马古道的文化介绍
2. 有关云南茶马古道的导游词
3. 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历程
4. 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研究毕业论文
5. 浅析当代中国云南茶马古道沿途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6. 茶道的传播
对于藏区的行政机构设置,明朝先后在西北藏区设立洮、河、岷、西宁四卫,在今甘、青、川部分藏区以及卫、藏地区设置“朵甘卫”和“乌思藏卫”。1374年,复于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同时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明太祖为此下诏晓谕诸部:
同时分别任命管招兀即儿和锁南兀即儿为乌思藏、朵甘都指挥使司同知,并赐银印。后又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1375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
明朝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后,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明朝在藏行政规划 都指挥使司 乌思藏、朵甘 明史对治
藏而
设置
的行
政规
划的
记载 指挥使司 陇答 宣尉使司 朵甘、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 招讨司 朵甘思、朵甘陇答、朵甘丹、朵甘仓溏、朵甘川、磨儿勘 万户府 沙儿可、乃竹、罗思端、别思麻 千户所 朵甘思、所剌宗、所孛里加、所长河西、所多八三孙、所加八、所兆日、纳竹、伦答、果由、沙里可哈忽的、孛里加思、撒里土儿、参卜郎、剌错牙、泄里坝、润则鲁孙 明朝在安多藏区的行政建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卫所,一方面承认世居其地的土官酋豪的世系特权,一方面派遣汉族流官,以流管土,以土治番,土、流官员皆为武职,听命于兵部调遣。
按明朝官制,军职流官分八等,即: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留守;而土官则分九等,即: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试百户。自都督府、都指挥司以下各司,包括土司,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各统其官兵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但土司之管有如佥事、镇抚、千户、百户等皆无岁禄。各卫所的统辖大权一般都由汉族流官掌握,土官只是“为之佐”。但这一情况在1437年二月发生改变,明朝开始给陕西河州、洮州、西宁等八卫土官发放俸禄。
总的来说,整个安多藏区都在陕西布政司辖区之内。明朝在安多藏区设置的卫所在明朝一代前后期变更较大,以下是明初在安多设置的卫所:
西安行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西北疆域总的军事机构。1374年七月置,治所位于河州,宁正为都指挥,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1375年十月改名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西安。1376年十二月罢之,1379年正月复置于庄浪,1393年移至甘州。
河州卫,1371年正月置,治所于河州,初以宁正为指挥使,锁南普为同知,朵儿亊、汪家奴为佥事,下辖八个千户所、一个军民千户所、七个百户所、两个番汉军民百户所。
岷州卫,1378年七月由岷州千户所改置,1382年四月升为军民指挥使司,1545年置州,改军民指挥使司为卫,1561年闰五月,废州重置军民指挥使司。
洮州卫,1379年二月由洮州千户府改置。洮州大土司卓尼杨于1404年投明,1418年被授世袭指挥佥事。洮州另一咎姓大土司亦是于永乐三年被赐姓“咎”,辖藏民七十六族。《洮州卫志》称“(杨、咎)二部称雄,诸番畏之”。
甘肃卫,1372年十一月置,治所于甘州,1390年十二月以甘肃卫为甘州卫,1392年置甘州左卫。1393年移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甘州,辖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
西宁卫,1373年正月置,故元同知李喃哥世袭为指挥佥事,故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儿只失结为指挥佥事。1432年升为军民指挥使司。西宁卫有达13个大土司承袭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三职,关西七卫中有五卫隶属于西宁卫。
必里卫,1403年由必里千户所改置。《嘉靖河州志》记载该卫未设指挥使,仅有掌牌指挥二员、掌牌千户五员、掌牌文户十四员、镇抚一员。
除了设置卫所,明朝还封派皇族子弟到安多藏区就藩,如1391年明太祖封十八子庄王朱楩于岷州,1392年封十四子肃王朱楧于甘州。1395年正月丙午,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兵助封于秦州的秦王朱樉征洮州叛番,由此可知分封的藩王是直接插手管理安多藏区的事务的。
明朝还在宗教寺院周围设置卫戍。比如岷州卫的大崇教寺,因其地位显赫,岷州卫动用其七分之一的士卒予以护寺。
为了协调安多藏区佛教与朝廷的关系,明朝在安多一并设置番僧纲司,较重要的有:
西宁、河州僧纲司,1393年三月置,僧人三剌、月坚藏分别被授予都纲之职。
洮州僧纲司,下辖垂巴寺赵僧纲、著洛杨僧纲、麻儿司马僧纲、圆成寺侯僧正、阎家寺阎僧正。
岷州崇教寺僧纲司,明成化年间置,班丹扎释世袭都纲之职。
庄浪卫僧纲司,由阎姓喇嘛世袭都纲之职。
禅定寺僧纲司,由洮州卫指挥佥事杨土司兼任僧纲。 明朝先后派许允德、克新、巩哥锁南等前往朵甘、乌思藏招抚。1370年,康巴藏区的故元镇西府武靖王主动向明朝左副将军邓愈请降,后入觐。1371年十月,明朝在康巴设置朵甘卫指挥使司。1371年二月,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带领大批故元旧官来朝进贡,乞授职名。于是其人分别授予了朵甘卫的指挥、佥事及其下属机构的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职。其中,锁南兀即尔被任命为朵甘卫指挥佥事。同年十月,在送交故元司徒印后,锁南兀即尔被升任为卫指挥同知。1373年,朵甘卫和乌思藏卫一同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管招兀即尔为都指挥同知。同年十二月,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以赏竺监藏等七人为朵甘都指挥同知。
在明朝任命当地政教首领行使官府职能的同时,明朝还掌握对当地官员升迁、承袭权力过程中的的审批、允准权。如1430年五月,朵甘都司都指挥使撒力加监藏上奏朝廷,称年老乞致仕,请求以其子星吉儿监藏代职,明廷乃从其请;1441年四月,朵甘都司大小首领派使入朝,上奏都司内部的人事变更事宜。等等。
●朵甘宣慰使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1374年十二月置。初任命星吉监藏为宣慰使司宣慰使。1385年正月,明朝定其官员品级为秩正三品。
●陇答卫指挥使司,辖地为今西藏自治区江达县西北隆塔一带,1373年置。1406年三月,巴鲁被任命为陇答卫指挥使。对于卫署官员的任免,依明朝袭替规定处理,多为世袭或当地土酋担任。陇答卫数次受朝廷之命与乌思藏的帕木竹巴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等,“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
●董卜韩胡宣慰使司,辖地为今四川宝兴一带,1415年六月置,南葛为首任宣慰使。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辖地为今四川康定,1397年置。该宣慰使司的设置结束了元朝鱼通、宁远、长河西三地各自为政的局面。
●武靖卫指挥使司,辖地为康巴宗多地方,1372年置,故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为武靖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
●陇卜卫指挥使司,辖地位于今玉树地区以东,濒通天河下游西岸,1413年置,初以锁南斡些儿为指挥使。
●毕力术江卫指挥使司,辖地为今玉树州治多县境内,1434年置,以官著儿监藏为卫指挥使司、阿黑巴为指挥佥事。
●朵甘思招讨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1374年十二月置。1385年正月,明朝定其官阶品第为正四品。
●朵甘陇答招讨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1374年十二月置,其官署人员按明朝土官袭替规定承袭。
●朵甘丹招讨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邓柯一带,1374年十二月置。
●天全六番招讨司,1373年十二月置,秩从五品。1388年二月,天全六番招讨司改为武职。
●朵甘仓溏招讨司,辖地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境内,1374年十二月置。
●朵甘川招讨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1374年十二月置,其官署人员按明朝土官袭替规定承袭。
●磨儿勘招讨司,辖地为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1374年十二月置,其官署人员按明朝土官袭替规定承袭。
●朵甘直管招讨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北部,弘治年间置,其官署人员按明朝土官袭替规定承袭。
●沙儿可万户府,1374年十二月置,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管者藏卜为万户府万户。
●乃竹万户府,1374年十二月置,辖地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贡觉县。
●罗思端万户府,1374年十二月置。
●别思麻万户府,1374年十二月置,辖地为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剌麻监藏卜为万户府万户,后被授指挥佥事职,其官署人员按明朝土官袭替规定承袭。 1372年四月,河州卫向明廷进言,“乌思藏怕木竹巴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人所信服”,建议朝廷招抚之。中书省将此建议上报,得到明太祖的允准,“诏章阳沙加仍灌顶国师之号”。章阳沙加即乌思藏帕竹政权的第二任第悉释迦坚赞,这次封赏赐印是明朝建立一来首次册封乌思藏首领。1373年正月,章阳沙加即遣锁南藏卜向明朝朝贡。同年二月,乌思藏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亦亲自入朝,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同时荐举的六十名故元旧官皆被授以官职。
1374年七月,明朝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从乌思藏返京的使者向明太祖报告,“各官公勤乃职,军民乐业”,因此下诏,“尚虑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兹命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其朵甘、乌思藏亦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颁授银印,仍赐各官衣物。”1375年,明朝再置俄力思军民万户府、帕木竹巴万户府,乌思藏笼答千户所,设官十三人。此处的俄力思即为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由此明朝完成了全藏的招抚任务。
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人员的分封,大部分是应求封者的自我介绍而封授的。从数量上看,基本上是以俗官为主而僧官为辅;从官职品级上看,此时期封赐的等级也普遍较低,最高仅为“大国师”和“灌顶国师”。在藏地封授的官职、封号大多是沿用元朝的旧称。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
明朝所封的各教王在袭职嗣位元需要请示明廷的批准。如1423年,为了审查第五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番僧班丹扎失受明朝委派前往藏地工布的咱日山,“审查大宝法王的呼毕勒罕”,这是中央王朝审查藏传佛教教派转世灵童的最早记录。
巴卧·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中记载:“依皇帝(指明成祖)本人思维,动用军队,仿行元代故事,将乌思藏纳入法治”,但大宝法王认为佛法应“自在自如宣扬,不便派遣汉军前往”。面对明成祖意在仿效元代萨迦派故事,独尊噶玛派,大宝法王认为“倘教派独留一家,众生不服,如听随其各所信奉,则必感动佛发慈悲心矣,故听任各自奉行各自之教法,斯乃适当。”
帕竹政权在藏内创立“宗本”制度,明代史籍中称“宗”为“寨”。永乐时期,藏内各宗已经为各大家族所把持,因此明朝就势对各宗本予以分封。如1413年二月置乌思藏卫牛儿宗寨,即为帕竹政权的乃东宗。1416年五月置领思奔寨,即仁蚌宗,所封官员喃葛加尔卜即为宗本南喀杰波。
因为元末战乱,藏内的驿站一度陷于废弛状态。因此,1407年三月明成祖下令命帕木竹巴阐化王,“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答王(三)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谕令发布后,明成祖同时“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1414年又派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谕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以及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驿站恢复之初,明廷为减轻驿站马匹困难,谕令以征发之马或军马拨给差民使用。同时在旅途中发放“道里费”,以解民困。经过多年的努力,藏内的驿站全部得到恢复,“自是道路毕通,使者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1373年,乌思藏帕木竹巴的第悉章阳沙迦应招遣使进京,同时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亦亲率使团来朝,向明廷荐举六十名藏地首领。在此情势下,明太祖依照内地卫所制度在藏区设立了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朵甘卫指挥使司,同时设置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乌思藏卫指挥使司辖区为卫、藏地区。依明制,设置卫指挥使一员,正三品;卫指挥同知二员,从三品;指挥佥事四员,正四品;卫镇抚二员,从五品。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为首任指挥同知。
1374年七月,明朝升乌思藏、朵甘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颁授银印,赐各官衣物,明太祖诏谕“劝赏者,国家之大法;报效者,臣子所当为。宜体朕心,益遵纪律”,并任命管招兀即尔为乌思藏都指挥同知。依明制,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一,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
1374年十二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和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进京朝贡,上奏第二批举荐人员名单,请求授予赏竺坚藏等五十六人官职。明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患,故来者辄授官”。
●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1374年七月由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升格而成,其为明朝在乌思藏的最高行政机构。
●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俺不罗”即为“羊卓”,辖地在今西藏浪卡子一带。明初设置俺不罗卫,后升为行都指挥使司,置于乌思藏之下,由乌思藏都指挥使监管事务。1385年,古鲁监藏被任命为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机构官员之任职由其后人或家族成员担任。
●乌思藏宣慰司,1373年二月置,隶属于乌思藏卫行都指挥使司。
●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牛儿宗”即“内邬宗”,辖地在今西藏拉萨市西南之堆龙德庆县境内。1413年置,喃葛监藏被任命为行都指挥佥事。
●领思奔寨行都指挥使司,“领思奔”即“仁蚌”,辖地位于后藏。1416年置,喃葛加尔卜被任命为行都指挥佥事,并封“昭勇将军”。
●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俄力思”即“阿里”,辖地为今西藏阿里地区和拉达克。1373年二月,搠思公失监被任命为元帅府元帅。1375年,俄力思元帅府与帕木竹巴万户府、笼答千户所一并正式成立。
●必力工瓦万户府,“必力工瓦”即“止贡”,1385年正月,其官员品第被定为秩正四品。1413年,止贡首领领真巴儿吉监藏被封为阐教王。帕木竹巴万户府,1375年置。1406年,
●帕木竹巴首领剌思巴监藏巴藏卜被封为阐化王。
●仰思多万户府,辖地在今西藏江孜一带。1382年,公哥怕为万户府万户。
●巴者万户府,辖地在西藏昂仁以西。
●沙鲁万户府,辖地在今西藏日喀则东南初的夏鲁。1397年,列思巴端竹为万户府万户。
●著由万户府,辖地在今西藏隆子县境内。1409年二月,搠巴星吉卫阿儿的占为万户府万户。
●加麻万户府,辖地位于盆域。1379年二月置,端竹监藏为万户府万户,并封“信武将军”。
关于“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溥成娟]投稿,不代表绿康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nmgjkcy.com/lukang/175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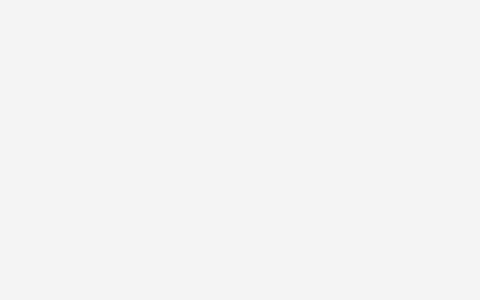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绿康号的签约作者“溥成娟”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文章不错《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内容很有帮助